新春大喜!
雷老師復出臉書,2.0更加康健。
再沒更快樂的事了。
鼠年真好年!
雷老師復出臉書,2.0更加康健。
再沒更快樂的事了。
鼠年真好年!
--
我們老輩習慣香港的書之設計:當然董橋的文章和食是比較集中
董橋 [著]《白描》2004 / 《小風景 》2003 2003.6.2~2001.11.1
272 頁 胡適錄貫酸齋《清江引 》 (寫給充和、漢思; 1987.4 充和送黃裳)
小風景:知識分子幫甚麼閑! | 蘋果日報| 要聞港聞| 20030122
narcoleptic desperation 董橋 《小風景 》 末篇2001.11.1
narcolepsy
The term narcolepsy derives from the French word narcolepsie created by the French physician Jean-Baptiste-Édouard Gélineau by combining the Greek νάρκη (narkē, "numbness" or "stupor"),[4][5] and λῆψις (lepsis), "attack" or "seizure".發作性嗜睡病(Narcolepsy),又名猝睡症、渴睡症,是一種睡眠障礙,與睡眠機制相關的異常。最早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的附屬醫院發現。
~~~~
雲樹,寧石,蒼草,一對斑馬閑佇河邊飲水,瑩閃著身上天繪般美麗線條,粼悠的時間之河,無所甚悉的殘鏤晴白,遼吟著自由與記憶。
雷驤 木刻版畫黑美人 All Beauty
https://vimeo.com/135434813
昨天看【愛悅讀】庫存片 才知道有雷驤著作傅月庵編的【人間自若】
【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
這套書限量印 2888 套 每套編號 附雷驤版畫【人與馬】卡片 寫著
我的繪畫與寫作
始於察知一己生命的侷限
作品只有當與讀者相遇
才是實質意義上之「完成」
我對北投有些感情 所以在某書店看到編號586的 就笑納之
(書中夾有前一位主人二張摃龜之威力彩)
~~~~~~~
****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雷驤 著作【人間自若】傅月庵 編 臺北:掃葉 2015
北投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林布蘭之家」買到整套的「林布蘭自畫像」的複製品。那原是以銅板蝕刻做成的;各幅表情殊異:有的發嗔;有的發噱;有怒目相視的,也有卑恭乞憐的。我想像畫家面對著鏡子擠眉弄眼的樣子,以求得同一副五官臉型卻呈現全然不同的模樣。
這與林布蘭正式的油彩自畫像十分不同,那厚重的衣飾與空間的光調,一切符合油畫顏料的表現特性。
也許目的在於研究人物表情的變化,整套蝕刻自畫顯示了畫家的各個面向,以至於我們變得十分熟悉他,猶如多年老友。
傳世的林布蘭生涯圖畫中,有一幅是他撥划著草編的筏子,在運河河道滿布的郊野,手持畫本寫生的樣子。
作家的 幻想與旅行虛實記述。—原刊於聯合報副刊
『那個夏天,我靠著堤岸,倏忽見一條舟艇自橋涵駛出,之上有七八個年輕男女,那是從歐洲各地來此度假的孩子,他們之中有幾個赤裸的背曬得通紅,緩緩滑過堤上一座銅像,一座抱胸垂地的昂立向天的巨像,古典的雙分捲髮及肩,一隻高挺的巨鼻,那是猶太裔的哲學家史賓諾莎。
白雲藍天敞開其上。』
UDN.COM
雷驤/飛翔。林布蘭 | 聯合新聞網:最懂你的新聞網站
2016年,我摘除胸腺瘤手術後,住院近117天,在最初住加護病房的5
傅月庵──和駱以軍。第22屆臺北文化獎【推廣講座】:〈人間自若皆有情〉
時間:11月17日(六)15:00-16:00
地點: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2F(臺北市同安街 107 號)
與談人:駱以軍、傅月庵
嘉賓:雷驤老師、Amy師母
***
明天(週日)雷老師要到愛樂電台『聲音紡織機』節目受訪,跟各位說第一次在家請客的故事,14:30開始,歡迎收聽。
——————————
初宴(原文刊載於「文訊」雜誌。)
那是Amy同我結婚成家後,第一回款宴友人吧,如果那簡陋粗疏的餐食調理也能稱之為「宴」的話。
1967年秋末的黃昏,我爬上淡江文理學院的長階,《文學季刊》的朋友四、五位迎面而來,我是專為迎接他們來淡水家中便餐的。以陳映真為首,應學生社團之邀前來講演──為打開《文季》這份頗為孤獨的文學創作刊物的銷路。
我看著他們幾個在黃昏的水泥道上走來:尉天驄和映真笑著;裹著皮草大衣的施叔青幾乎是跳蹦地走;吳耀忠卻端肅著臉邊吸紙菸;另外還有當時社團分子的王津平和武允恭等來相送的三、四個同學──這一幅時代文學青年的圖像,很讓我不能忘懷。
這時匆匆從後面趕來的學校總教官,一稍後聽到了消息,有點疑慮地走來打招呼,大約想盤問講演內容,而映真機敏地以「手掌滿是粉筆灰」為由,婉拒了總教官伸出的手……
妻Amy在我們租住的地方預備好幾道家常菜,我特意來為客人引路,以便順利抵到不容易找的鎮上稱做「布埔頭」的小樓。當時我們家每日肉類預算只能支付新台幣三元,這樣一位家庭主婦能做出什麼特色盛饌,我是沒有所指待的,只不過盡一份住淡水文友的地主之誼罷了。
我是《文季》第五期才加入這個文學團體的,此後每期寄稿,直到第一階段《文季》的結束。這份同仁雜誌先有四期,因為是季刊,所以已發行了一年。說起來我會在《文季》的出現,係仰賴七等生的中介,他將我寫〈犬〉小說原稿,不具名地轉給映真,立即獲得《文季》諸人的讚賞──以為是七等生當期的新稿件。我們年輕時代悲運的相繫,是七等生與我的書跡十分相近之故。
現在很難回溯初宴《文季》的友人中,那時一直往還密切的七等生缺席的原因,尤其兩家家眷也曾十分熟識。
想起來這邀宴可算是對《文季》同仁的一種答謝──自從加入這個文學團體以來,頗有一些受邀宴飲的機會,大抵二、三個月一回,如同發刊例會似的聚餐。當時,寄稿者畢集,奉為精神領袖的姚一葦師也會蒞場。聚會記得有幾次是利用長輩不在時的丘延亮家日式大宅舉開,負責全席料理的則是一名叫「單槓」的台大醫科學生,筵席菜色正典,很難想像出自那麼一位沉靜的醫科學生之手。
當時《聯合報》藝文版名記者楊蔚也經常列席,此一時期,他為本地前衛藝術家寫的個人專介,引起人們興味的眼光,掃視到這個當時十分寂寞的角落來。兩、三年之後,情治單位破獲文化藝術界「叛亂」大案,原來即記者楊蔚長期臥底調查的結果。醫學生「單槓」、丘延亮、王小虹以及「初宴」應邀的文友陳映真、吳耀忠皆涉獄,當然這是後話了。
《文季》平時談發行、約稿、校稿的所在,於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廊前有周夢蝶先生擺設的書攤),那二樓幾成了「文季編輯部」,付款的東道主總是老編尉天驄。即使是咖啡廳淡而無味的「簡餐」;或是隔壁排骨大王油膩的菜飯,予我都是值得感念的盛饌了。
「雷驤的身邊,都時常有一位看來才高中生那麼大,安靜而美慧的妻子。」映真後來為我的小說集出版寫序的時候,這麼樣說:「總之,如果當時還不是妻子,畢竟不久就結婚了。」
我倆像受命於父母的安排(實際已有三年「自由愛戀」的經過),悄悄在故鄉行禮與宴請之後,便返北租貸了小街上前樓的一間房,這麼樣開始生活。
大約這也是一成理由──為得到文友們的祝福,而補上這次的吃飯吧。
由窄木梯走上來,前邊有四扇窗的七席半的一房,而靠窗的一端,愈走愈低矮,最後只能座落窗台了,便是我們的居處。想像Amy每送我出門上班以後,便坐著向窗外觀看,以度過寂寞的一日。得了屋主的允許,共用樓下廚房一角,安置我們那隻野營用的小瓦斯爐,簡單地烹煮後,用托盤端到自己房裡,跪坐在塌塌米上,圍坐茶几邊上吃的。
隔著一層木板壁,獨居著一位和善的老先生,就是房東的父親,時時傳來哮喘和輕咳。房東說:父親久已聾了。
那一次,因為沒有餐室的「宴請」是不可能的,屋主破例讓我們使用樓下的客廳宴客──那裡有L型沙發組以及長矮几,隔著小小天井,尚可透見廚下忙忽的Amy的身影。
朋友們坐落那借用的空間,是否感到怪異或不安,我們無從顧及。文友們一體面向著天井,透過雙重玻璃窗看向廚房,似有一種娛樂效果。
「像繡花似的」──施叔青這麼樣描述Amy面對烹具而躊躇的模樣。那時還是法文系(西洋與文學系法國語文組)三年級的施叔青,理應自己也沒有烹煮經驗吧。
Amy終於來排碗筷了。原屬我兩人的食具,顯然不足請客,記得預先添購了幾隻碗。
群客們當時及後來的生平,在此略為介紹:
尉天驄,《文季》主編,時任政大講師。之前已創辦過思辨性雜誌《筆匯》。2019年12月逝世於台北。
陳映真,天驄《筆匯》時代崛起的小說家,《文季》創刊人之一,時在竹圍「輝瑞」藥廠工作。稍後,因難「白色恐怖」判刑十年。2007年後在北京定居,曾於「人民大學」駐校。2016年11月逝世於北京。
吳耀忠,國立藝專美術科助教,映真年少時代摯友,並為《文季》之友。「白色恐怖」同案繫獄,釋出後一度任「春之藝廊」經理,1987年因酗酒抑鬱而終。
施叔青,淡江文理學院學生。後來的知名小說家,一度長居香港,曾任「香港藝術中心」主任,現居美國。
武允恭,淡江文理學院數學系學生,後移居美國。
王津平,淡江學生。後任「勞動黨」黨委會書記長。當天有事先離開,並未留飯,2019年9月逝世於北京。
飯菜排列開來,大約有蒸魚、紅燒茄子與菜脯蛋等幾樣平常菜餚。因為沙發前的長几並非食桌的高度,五個客人居長沙發那一邊,主人的我倆搬來腳凳面對面坐著,每個人舉箸甚遠──這距離往返挾菜,就食的印象大致如此。
文友們似乎津津地、默默地食著,口中沒有溢美的讚詞,當然我們原也不敢奢望。
記得之前有一回,七等生約我和映真去他家晚飯,從淡水線石牌站下車以後,夜暗中摸索行過許多小路,最後繞行晾在院落裡的幾幅被單,才見合院廂房亮著燈光,七夫婦已守候多時。以為慎重的約請必有相配稱的盛餐,食桌上卻也只平素疏淡的飯菜而已,這也無非是六、七○年代一般人的生活。當然此行為了「看看老七婚後的生活」目的已達。映真爽快地以菜湯泡飯,呼嚕嚕的吃出聲響來,大約為了讓主人安心吧。
我家的初宴,客人們的反應大約也有類似的表現。
那天映真留下一則笑話,仿起地道的四川話,學他的師長說:「永善哪(映真本名),不是你的頭太大(映真綽號「大頭」),是天堂的門太小囉!」
深秋的天光,在吃食中很快的暗下去,送別文友們到庭前的矮門,回望室內已亮著綠白色的日光燈,朋友們的背影轉出清水街口匯入中正路,那麼距離昔日的淡水線火車站,只有一箭之遙了。
最近有一次去淡水,路經清水街口的時候,忽然憶起舊往的事,文友們之後的遭際與歧路,不免令人嗟嘆,那座39年以前我們曾「設宴」的小樓,在如今雜沓到幾乎很難通過的路口,已經找不到了。仔細辨思,大約就是現今翻造成貼粉紅色磁磚的那一幢吧。
不知怎地,在眾聲喧鬧裡,彷彿我還聽見,昔年隔壁老先生哮喘和咳嗽的聲音。
原稿寫於2007年,2020年5月修畢
******
......今天掏到以前水晶唱片的業務 林崇予傳給我的罕見罕見罕見封面,雷光夏首張專輯「我是雷光夏」的日本版CD封面。看,創作是病毒,到日本去了。日本版額外收錄「泰雅人的故鄉」。音樂往留言1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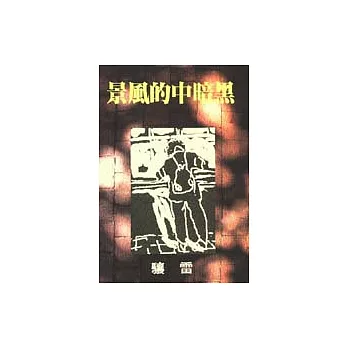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