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允芃 小檔案
殷允芃 /天下雜誌發行人 ...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
學歷:成功大學外文系、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 經歷: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駐台記者,以及《亞洲華爾街日報》特派員;並於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
榮譽:1976年,獲選十大傑出女青年;1987年,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美譽的「麥格塞塞獎」;1995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2010年,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終身成就獎。並曾多次獲頒金鼎獎。
作品:《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新起的一代》、《決策者》、《太平洋世紀的主人》、《等待英雄》、《點燈的人》、《發現台灣》(合著)、《敬天愛人》、《素直的心》;並執導《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紀錄片
殷允芃:《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問錄 》( 1982)
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封面. 書名: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 作者:殷, 允芃著; 叢書:
張愛玲獨家專訪 華人世界絕響

作者:殷允芃 2015-09-14 Web Only
調整字體尺寸
80年代,遠在洛杉磯的61歲張愛玲捎卡片給《天下雜誌》。她與《天下》的緣份,起於創辦人殷允芃還是窮留學生時,穿著借來的棗紅色牛仔褲採訪她,這個採訪,成了華人世界的絕響。
那一天,雨勢悄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臺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粧檯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三藩市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得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要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于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夷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慧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霜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 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贊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一一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于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像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像。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游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仿佛荒山古廟裡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蟋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惟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人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看法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仿佛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臉,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發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淤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你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你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裡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臺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
附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 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面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臺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族,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 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表現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有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 See more at: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0847&utm_source=FB&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FBdaily#sthash.s6BpF0D5.dpuf
******
究竟與中國簽不簽訂所謂的"服貿協議",我個人的一項準則是,如果《天下雜誌》等能夠
在中國發行,可簽。不然,就擱置它。
40年前的新潮文庫版本叫《中國人的光輝:當代名人訪問錄》台北:志文,1971;台北:天下雜誌,2011
現在這些生命的故事仍然讓作者與讀者有生之勇氣.....(2011)
2014.11 在舊書攤買到1977年的再版本,重溫此書,很感動。譬如說第一篇的訪問張愛玲: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殷允芃從記者到媒體集團的主人
正如李登揮從學者到總統
見證如此多的台灣人的光輝
----
希望—— 永遠在路上
(殷允芃)
是一個清風微涼的下午。在台南孔廟的邊殿,有一幅蒼勁的書法。跟著默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唸錯了,是「事有終始」。
頓然領悟: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怎麼開始走?
這豈不也是在台灣的人,經常抱怨的現象 —— 大學生常問:「我未來要做什麼?」知識份子常批:「國家沒有願景,沒有方向。」一般人焦慮:「明天是否會更好?」
什麼是台灣不同的路?
也有人期待,台灣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但什麼是台灣的不同的路呢?
仔細回顧、認真觀察,其實台灣已然在路上。雖然仍步履蹣跚,雖然路上仍有荊刺待砍,但這條顛簸的路已隱然成型。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多次的政黨輪替,已使人民對民主多了點信心,也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選舉輸贏。只是多數政客仍習於將制衡當成你死我活的鬥爭。
相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上層結構與機制,仍需深化與優化,人民的自主力量與民主素養,已更明顯的躍升。
人民已習慣由下到上的推動社會進步。不只是抗爭,掙權益,也能以參與式的民主和政府形成伙伴關係,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人民不僅有力量,更有行善的力量。
頓然領悟: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怎麼開始走?
這豈不也是在台灣的人,經常抱怨的現象 —— 大學生常問:「我未來要做什麼?」知識份子常批:「國家沒有願景,沒有方向。」一般人焦慮:「明天是否會更好?」
什麼是台灣不同的路?
也有人期待,台灣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但什麼是台灣的不同的路呢?
仔細回顧、認真觀察,其實台灣已然在路上。雖然仍步履蹣跚,雖然路上仍有荊刺待砍,但這條顛簸的路已隱然成型。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多次的政黨輪替,已使人民對民主多了點信心,也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選舉輸贏。只是多數政客仍習於將制衡當成你死我活的鬥爭。
相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上層結構與機制,仍需深化與優化,人民的自主力量與民主素養,已更明顯的躍升。
人民已習慣由下到上的推動社會進步。不只是抗爭,掙權益,也能以參與式的民主和政府形成伙伴關係,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人民不僅有力量,更有行善的力量。
台灣的志工文化,使得海灘鄰里更清潔、醫院更親切;環境更優美、圖書館與博物館更親民,偏遠地區的小學生也能得到閱讀的協助。志工文化更增加了社會溫暖的底蘊。
普羅大眾的善心助人,不論是賣菜的婦人陳樹菊,或退休的老兵洪中海,都成為世界媒體競相報導的台灣特色。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南投偏遠山區原住民為主的長福國小,只有四十一個學生。六年級畢業班的八位學生,受到一本書的感召,決定要想辦法募款,為遠在四千里外,尼泊爾波卡拉山區的一個窮困村落,建儲水槽。因為當地缺乏乾淨的水源,近五分之一的小朋友因瘧疾染病而死。
這八位小學生將自己的繪本編印成書,到處義賣,募得十一萬台幣,捐建水槽。他們選擇把做成這件事,當成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世界有災難的地方,就有慈濟人領先趕赴埋鍋燒飯。加上近年各宗教團體推動的「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和「微笑台灣」運動,慢慢移風易俗,台灣人民的友善,逐漸成為外來客最明顯的台灣印象。
計程車和公車司機,與乘客下車時的互道謝謝,捷運車上的競相讓座,也已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一位大陸財經媒體的負責人,來台參訪後忍不住稱奇:「怎麼好像到了君子國。」
美麗之島,也是善心之島
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路經台北市綠意蔥蔥的敦化、仁愛、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幸福感和驕傲感自然而生。鄉鎮和鄰里也競相種樹植花,整潔與美麗漸漸成為人民的生活共識。
普羅大眾的善心助人,不論是賣菜的婦人陳樹菊,或退休的老兵洪中海,都成為世界媒體競相報導的台灣特色。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南投偏遠山區原住民為主的長福國小,只有四十一個學生。六年級畢業班的八位學生,受到一本書的感召,決定要想辦法募款,為遠在四千里外,尼泊爾波卡拉山區的一個窮困村落,建儲水槽。因為當地缺乏乾淨的水源,近五分之一的小朋友因瘧疾染病而死。
這八位小學生將自己的繪本編印成書,到處義賣,募得十一萬台幣,捐建水槽。他們選擇把做成這件事,當成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世界有災難的地方,就有慈濟人領先趕赴埋鍋燒飯。加上近年各宗教團體推動的「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和「微笑台灣」運動,慢慢移風易俗,台灣人民的友善,逐漸成為外來客最明顯的台灣印象。
計程車和公車司機,與乘客下車時的互道謝謝,捷運車上的競相讓座,也已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一位大陸財經媒體的負責人,來台參訪後忍不住稱奇:「怎麼好像到了君子國。」
美麗之島,也是善心之島
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路經台北市綠意蔥蔥的敦化、仁愛、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幸福感和驕傲感自然而生。鄉鎮和鄰里也競相種樹植花,整潔與美麗漸漸成為人民的生活共識。
希望—— 永遠在路上
當然,在林蔭大道的背後,仍有破敗的舊屋;在巷弄間令人驚豔的創意商店旁,仍有生鏽的鐵窗和零亂的電線。但美麗台灣,已漸漸成為大家的願景。
美麗台灣,不僅是山川美、水岸美,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美。
「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是觀光局新推出的台灣Logo,希望觀光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心和溫暖。美麗之島,也可以是善心之島。
做為海洋中國的前沿,台灣正領先擁抱世界,以民主、自由、多元、包容、尊重、環境永續,走向一條追求美麗的道路。希望也以這個美麗的試驗,為華人、為亞洲、為世界做出貢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美麗台灣,不僅是山川美、水岸美,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美。
「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是觀光局新推出的台灣Logo,希望觀光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心和溫暖。美麗之島,也可以是善心之島。
做為海洋中國的前沿,台灣正領先擁抱世界,以民主、自由、多元、包容、尊重、環境永續,走向一條追求美麗的道路。希望也以這個美麗的試驗,為華人、為亞洲、為世界做出貢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真誠如實且善意的人物寫作,能讓人得到滋養與望
1941年生的殷允芃,在197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今年是本書出版40年,天下雜誌以全新的封面及編排,再 度推出上市。本書收錄她留美期間採訪當代傑出華人及日本、美國名人的特寫報導,當時開啟了台灣深度人物特寫的先河,且在台灣新聞寫作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尤其在當前以揭人隱私為樂的惡質新聞環境中,本書的再版,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極具意義。全書收錄了19位名人的採訪紀錄,包括知名作家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賽珍珠、曾野綾子,學者夏志清,建築大師貝聿銘,外交家顧維鈞……等。文中展現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描摩,無論是喜歡閱讀人生故事的讀者、對或有意觀摩深度人物報導的新聞人,都不應錯過此書。
本書特色
深度人物特寫的經典、文學與報導交會的火花、新聞人必讀
天下雜誌群創辦人殷允芃採訪19位當代名人的訪問錄,包括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貝聿銘、曾野綾子、夏志清、馬思聰、顧維鈞……等。文中有詩的語言,歌的旋律,閱讀這些生命故事,可獲生命的滋養與希望。
本書是殷允芃女士四十年前出版之同名著作的最新版,全書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實為深度人物專訪的經典作品集。
出版緣起
殷允芃
重新出版當年在美國求學、任職時所寫的人物系列報導,不只為了記念那段初任記者時,充滿好奇的青澀歲月,也感謝那些樂於分享他們人生經驗的諸位受訪者。
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長河裡,我們得到了滋養與希望。
作者簡介
殷允芃
1941年生,山東滕縣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名譽文學博士。曾當選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並榮獲1987年麥格塞塞獎新聞獎、2010年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
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記者、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駐華特派,並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1998年創辦《康健雜誌》、2000年創辦《天下雜誌出版》、2000年創辦《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雜誌》。現任天下雜誌群創辦人、董事長兼總編集長。
除英文專作外,主要中文著作為:1971年《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1974年《新起的一代》,1982年《決策者》,1985年《太平洋世紀的主人》,1987年《等待英雄》,1992年《點燈的人》,1996年《敬天愛人》,1999年《素直的心》。
緣起:四十年後重新出版
訪:張愛玲女士
華爾街的紅人:蔡至勇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
設計製造電腦的:王安博士
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貝聿銘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音樂指揮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傑:楊蕾孟
廣告界的奇葩:楊雪蘭
文藝與科學兼長者:顧毓琇(一樵)博士
銀行界的奇才:吳棣棠
雪中旅人:聶華苓
作曲家:馬思聰先生
又見:於梨華
熱愛中國的:賽珍珠女士
愛荷華河上的:「金臂人」
榆樹鎮上: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印象 (殷允芃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
「櫻花戀」、「夏威夷」的作者:密契納
金盞菊的插曲
美國婦女們爭些什麼?
後記
訪:張愛玲女士
華爾街的紅人:蔡至勇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
設計製造電腦的:王安博士
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貝聿銘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音樂指揮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傑:楊蕾孟
廣告界的奇葩:楊雪蘭
文藝與科學兼長者:顧毓琇(一樵)博士
銀行界的奇才:吳棣棠
雪中旅人:聶華苓
作曲家:馬思聰先生
又見:於梨華
熱愛中國的:賽珍珠女士
愛荷華河上的:「金臂人」
榆樹鎮上: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印象 (殷允芃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
「櫻花戀」、「夏威夷」的作者:密契納
金盞菊的插曲
美國婦女們爭些什麼?
後記
那天晚上,雨勢稍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妝祇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舊金山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起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是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 國最優秀、最重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於梨華女士更爽直的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泰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於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澈。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悲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的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那兒就帶到那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裹。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讚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嗄嗄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 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遊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彷彿荒山古廟裏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蜷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劃,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
「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的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瞼,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髮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 「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瘀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 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妳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妳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地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台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附 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她說: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方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那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悲劇,壯年夭折,也是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一九七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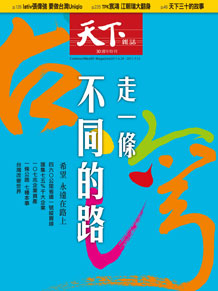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