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人均月薪1~2多萬元,台灣的書很少貴於200元,量、類也可觀,是閱讀的黃金年代。像 莊信正《異鄉人語》(1986),篇篇有內容,定價才100元。
現在,買當時出版的二手書,雖有微缺點,無關內容,還是閱讀的白金年代。這還牽涉到簡體字書,像《各在天一涯 : 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 / 叶嘉莹, 白先勇等口述》李怀宇采写 (2016),北京中華,462頁,進價才200元 (臺大圖書館),我看她(?)訪問傅申的,就值得了。
莊信正《異鄉人語》1986,篇篇有內容,很值得特別談談。
這是我2016年寫的:
以《異鄉人語》為例名家 (許達然或者莊信正等人)散文各集,其實可/值得作索引。莊信正自己或者他老師夏濟安針貶人多不寫人名,譬如說,兩處談陳之藩文章的問題。
本書至少三處提到胡適,書評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是全書之最;談他老師夏濟安確定他對胡適已經無惡評時,才給他夏濟安與胡適的合照 (拜壽時照的);另談中國的日記,民國期的,當然要提胡適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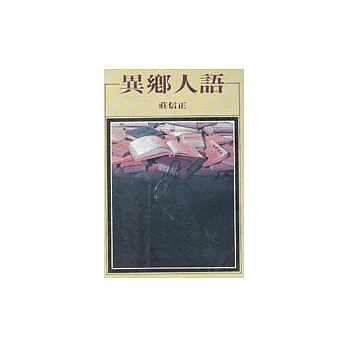
異鄉人語
作者: 莊信正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1986/04/01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簡介| 莊信正 - 東華大學
簡介
作家: 莊信正
性別: 男
籍貫: 山東即墨
出生日期: 1935年
來臺時間: 1949前後年
學經歷: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南加州大學、印地安那大學,並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從事研究,後於聯合國擔任翻譯工作,2005年曾任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駐校作家。現已退休,旅居美國。
文學風格: 莊信正的創作文類有論述和散文。論述多為研究喬依斯的專著,作品徵引豐富,深入淺出,篇題精簡,內容閎富,穿梭古今中外的學問,筆下縝密通達,最見積學修養。散文談創作與生命、小說與電影,描繪生活種種有趣與無奈,語帶幽默,散發著古今中外輝映對顯的知性和感性。莊信正所編《張愛玲來信箋註》,提供八十四封書信並詳加註解,對信的年代、內容背景做明晰的描摹,為「張愛玲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追憶陳世驤
追憶陳世驤
2014年01月31日 04:09中國時報
⊙莊信正
 1950年底陳世驤(左)與貝倫森合照。(莊信正提供)
1950年底陳世驤(左)與貝倫森合照。(莊信正提供) 陳世驤簽贈《親仁集》毛筆字的題詞。(莊信正提供)
陳世驤簽贈《親仁集》毛筆字的題詞。(莊信正提供)到柏克萊後知道陳先生第一個太太是音樂家姚錦新。老同事紀文勛先生告訴我這對夫婦非常瀟灑,不拘小節;家裡的擺設不重視觀瞻,餐桌的桌布髒了會翻過來用另一面。(後來的陳太太梁美真則有潔癖,全家一塵不染。)
我同陳世驤先生的交誼是從一篇文章開始的。
1964年3月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首府華盛頓舉行年會。陳先生當時任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教授並主持其中國研究中心的語文項目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而由我大學老師夏濟安實際負責研究寫作。那次陳先生擔任一個文學小組的主席,濟安、志清二先生提出論文。有一晚上我的台灣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校友洪越碧約我們幾個人去她家餐敘。屆時由我陪她丈夫John Fincher去旅館接陳、夏三位貴賓。歸程夏氏昆仲在後座用上海話連珠炮似地開懷說笑,我陪陳先生坐在前面,沿路他問了我的學歷和志趣。那晚連主人有十來個人,我們幾個晚輩(包括謝文孫和張灝)大都在洗耳恭聽;但我還是跟陳先生說了不少話。
其後沒有什麼聯繫。次年2月濟安先生以腦溢血猝逝。那時我正在堪薩斯大學任教,文孫來信說他在籌組一悼念專輯,邀我也寫一篇。4月去舊金山參加亞洲學會年會,過橋為濟安師掃墓,在會場內外見到陳先生幾次(他曾宴請幾個與會者)。5月我的〈才情、見解、學問──敬悼夏濟安先生〉和世驤、志清二先生的文章登在李敖主編的《文星》月刊。陳先生顯然進一步看出我同濟安師的關係和我對他的感念;從此我們開始通信,偶爾也通電話。
因為還沒有拿到學位,我在堪薩斯的職位只是visiting instructor(客座講師)。到第二年,有一次電話上談到我想另外找事,陳先生問我願不願意去他那邊。久仰他的品德學問,柏克萊舉世聞名,中國研究中心成就卓著,何況又是接濟安師的遺缺,我滿口答應。
暑假我回母校印第安那,在福爾斯特(Norbert Fuerst)師的監督下完成論文,通過口試;然後趕去柏克萊上任。這樣,開始了追隨陳先生的三年歲月。其間幾乎每天通電話,每周聚會;於是有機會深入瞭解他的背景,觀察他在處世和治學方面的一些特色。
●
單看他晚年在學院裡的形象不很容易想像陳先生先前的風頭之健。1936年他與英國著名文人阿克頓(Harold Acton,1886-1978)合譯的《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國現代詩選)出版。這是把中國新詩介紹給英文讀者的創舉。(阿克頓在序言中沒有交代二人合作的情況,倒是提到他不顧my collaborator的反對而收了林庚──事實上不但收了,而且以林佔的的篇幅最多,有19首;又特別請他寫了一篇文章談論對詩的看法附在小傳之後。)這24歲的青年從此嶄露頭角。他跟阿克頓後來又合譯過《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最後七場還沒有譯他便同濟安師一樣突然病歿;阿克頓無法單獨續完,後來由白芝(Cyril Birch)加工出書。阿克頓在回憶錄Memoirs of an Aesthete中讚陳先生為「我最親密的學生和合作者……。不但是英文很有造詣的成熟的學者,也是個開明的人文主義者」。並談到陳先生譯《文賦》時曾找他幫忙推敲;稱陳家是鬧市邊緣的幽居〈cloistral refuge〉;還說梁女士是an ideal wife。(經過阿克頓的引介,陳先生結識了美國著名藝術史家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1950年底去貝在佛羅倫薩鄉下的住宅,看到貝所藏李公麟《山莊圖》之一景。曾寫信談他對該畫的看法。)
●
陳先生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到美國雖然改授中文,卻同美國文壇頗有交往,結識了不少名家。他與賽珍珠夫婦相當熟稔。夏志清先生為《陳世驤文存》所寫長序裡敘述過他陪陳先生同凱岑(Alfred Kazin)餐敘的事。陳先生也同我談過那次夏先生面對他仰慕的這位批評家誠惶誠恐,十分緊張。陳先生比較要好的以詩人為多。例如忒特(Allen Tate)的書文遺檔中列有陳先生四封信。其時達納(Robert Dana)也在加大。我和陳先生在校園裡碰到過。他剛在《紐約客》上發表過一首詩,該刊在我心目中恍同經典,因而對他肅然起敬。也碰到過批評家蕭勒(Mark Schorer),看出他跟陳先生之間有超乎同事的交往。據志清先生相告,陳先生有一次來紐約,他們一起吃飯。席間有一美國詩人和她的私生子;那孩子長得像煞陳先生。(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母子的照片。)她的書文遺檔目錄中‘General Correspondence’下面有一條說‘Shih-hsiang Chen,1951-1963.Undated’。該是陳先生給她的一些書信。
尤其難得的是他同一老一少兩位名家的忘年交。1966年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把詩集Dear Men and Women獻給陳先生;那時他已高齡八十。至今我還記得陳先生多麼欣慰興奮。收到書後在簽送給我的這一冊裡用英文寫了幾句話,次年三月把書名譯成《親仁集》後又用毛筆字題簽,並工整地謄錄了他為譯名所寫一頁長的解說。
有一次陳先生請得意門生斯奈德(Gary Snyder)吃飯,叫我作陪。斯奈德在印第安那大學念過書,與我誼屬校友;當時已經成名。印象中他始終笑嘻嘻地,說話文雅隨和。過後看到他屢屢對業師表達敬意,稱他為a friend and teacher(亦師亦友);直承受過他深遠的影響。斯奈德說1955年選了陳先生關於唐詩的graduate seminar(專題研究),因而翻譯了寒山。「他熱愛詩歌,理解深切;他熱愛生命情調。他可以憑記憶引法文詩;隨便哪首唐宋詩詞他幾乎都可以默寫在黑板上」。斯奈德也提到陳譯《文賦》中的axe-handle proverb(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對他的啟迪。
●
到柏克萊後知道陳先生第一個太太是音樂家姚錦新(1911-92)。老同事紀文勛先生告訴我這對夫婦非常瀟灑,不拘小節;家裡的擺設不重視觀瞻,餐桌的桌布髒了會翻過來用另一面。(後來的陳太太梁美真則有潔癖,全家一塵不染。)但姚女士很左傾(她是中共要人姚依林的姐姐),而陳先生則堅決反共。加上別的原因,日久無法相容,姚堅持離婚,而陳先生不願意。據說由顧孟餘先生出面斡旋,雙方才達成協議;姚隨即返國定居(1947)。後來知道姚原先的男朋友是中共另一要人喬冠華,而因緣際會嫁給陳先生。
我手邊有他們夫婦婚後第一年合作的《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花鼓歌及其它中國民謠;1943)。對開本,64頁。其中〈花鼓歌〉二種佔三頁,其餘是民謠,如〈小白菜〉,〈孟姜女〉;由姚譜曲,陳譯為英文。也收了三首抗戰時期流行的歌曲。賽珍珠寫了短序。陳、姚各寫了導言。陳先生以摯愛的筆觸屢屢讚揚my beloved wife;說「愛妻」一絲不苟,歌詞要他翻譯多次才滿意。姚(英文名用了中國式的Chin-hsin Yao Chen)則未提丈夫,只謝了譜曲過程中相助過的人。她提到即將配合出唱片;但即使出過,現在恐怕也很難找到了。(上)
追憶陳世驤
稍後再讀
2014年02月01日 04:09中國時報
⊙莊信正
陳先生中等個頭,但舉止凝重從容,看起來很有尊嚴,彷彿比實際身量高。而即之也溫,容易親近。做人處事他是很成功的。
至少外表上陳、梁感情很好,生活平靜安適。陳太太是華僑,雖然普通話說得地地道道,卻不識字,不能看中文書,二人間少了一個重要的「共同語言」。陳先生兩次婚姻都未生兒女(人們都知道他喜歡認乾女兒),他愛熱鬧,又不再積極從事研究寫作,手中遂有太多的閒暇。他們夫婦都患嚴重的失眠症,晚上──尤其周末──打麻將習以為常。濟安師當年就幾乎每場必有。我對雀戰一竅不通,到柏克萊卻常在陳府三缺一的情況下濫竽充數;幾次之後漸漸產生興趣。那時候總覺得書讀得太少,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可以用來補習。我怕打牌上癮,更怕徹夜苦熬,於是找籍口能不參加就不參加。為了避免應酬,我往往用枕頭和毯子把電話重重疊疊遮蓋起來;雖然還是聽得到鈴聲,至少不那麼驚心動魄。沒有多久陳太太問我是不是故意不接電話,提到當年濟安先生日常去他們家的頻繁情況,說我也應當那樣。我很高興不把我當做外人。但這種待遇有其代價;有貴賓時我不但要奉陪,也要做司機開車接送。有的客人視我為幫陳先生辦事的門徒,態度倨傲,我不免會生悶氣。有一會畫畫的台灣立法委員去灣區;陳先生不知怎麼認識他,照例盡地主之誼。此人在什麼公眾場合「幸會」加州州長雷根,看來是硬上去自我介紹,拍了一張合照。他如獲至寶,當即在舊金山相館沖洗,要我開車帶他去取。雷根當時已經是我心目中最卑劣的美國極右派政客之一(他競選州長和當選後一個重要政綱是大幅度削減加州大學的預算),看到立委沾沾自喜的嘴臉我覺得厭惡,也有受到羞辱之感。
1967或1968年,一位著名華人學者去柏克萊教暑期班,陳先生更是屢屢熱誠款待。此人做學問很踏實,有成就,我早就買了他一本英文史學專著。及至見面,聽他談本行確有見地。記得他強調治學要能conceptualize(概念化),並提到中國方誌的重要性 和他對英國史學家陶尼(R.H.Tawney)的推崇。聽他唱曹操的「對酒當歌」,聲若洪鐘,抑揚頓挫,很有味道。
同時發現他喜歡用或隱或顯的方式自我表揚。陳家飯局很多;那個暑假他是座上常客,總要放言高論,目無餘子;往往惹人反感,甚至引起爭吵。有一次另一功力深厚的學者也在,對他每一論點都朗聲批駁:「你錯了」,「不是這樣的」。他終於勃然大怒叫哮起來,對方則老氣橫秋,夷然不動聲色;場面很僵。另有一次陳先生夫婦請他在中國飯館吃飯。席間他照例滔滔不絕。說得興起,提到有一年回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院會,有人通知他總統蔣介石要接見。「我見他做什麼?」於是不早不晚,選在接見前一天遠走高飛。當時聽了,不免替他難以為情。
由此聯想到陳先生的愛才。這從他先後禮聘顧孟餘、夏濟安和張愛玲三人去他那個研究計劃任職更可證明。(《論語》「親仁」二字的意思是親近有仁德的人。)顧先生德高望重,足可為中心增光。陳先生同濟安師卻並不熟,完全是由於欣賞他的才學。夏先生當然勝任愉快,為中心寫的幾本研究報告內容和文章都很精彩,應當結集出書。此前他歷經抗戰和內戰,窮愁潦倒。五十年代在台灣生活雖然安定,他一介書生,清苦如舊;而且缺少安全感,始終渴望離開。他沒有博士學位,在美國不容易找到教書的位置。柏克萊五年可能是他一生最平穩無憂的日子;尤其陳先生對他情同手足,使他有相知恨晚之感。(據紀文勛先生追憶,起初為濟安師立的碑上面只有陳先生而沒有志清先生的名字,經這弟弟當場抗議才加上。)可惜陳府聚會太多,尤其牌局往往通宵,濟安師又太要好,次晨不睡覺便直接去辦公室上班。這樣不但缺少時間讀書寫作,而且損害他的健康。(關於張愛玲,可參看我編的《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
我從夏濟安先生那裡早已知道中國中心那個崗位的職責,並仔細讀過他每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上任之前陳先生在書信和電話上更詳細地做了交代;我頗有新馬而已識途的信心。夏規莊隨,寫成了「處女作」呈交陳先生。他立即約我餐敘。到了飯館,他開門見山談那篇報告,居然肯定我的文字;我趕緊表示我的英文不行。他說還可以:「有一個style。」他當然知道這「風格」屬於新聞報導式(journalistic;夏志清先生也注意到),但彷彿認為寫那樣的題材無可厚非。我受寵若驚,同時感激他鼓勵後進的厚意。次年他看到我第二個報告的初稿,對其中一個較長的句子結尾一詞只有三四個字母提出批評,說該用較長的字眼,才能壓得住陣,避免頭重腳輕。當然是行家妥切的點撥。
正如阿克頓所說,陳先生的英文造詣很高。不過他極重感情,處理非學術性題材時筆下偶爾喜歡鋪張。濟安先生遺著The Gate of Darkness(1968;此書簡體字譯本《黑暗的閘門》今年可望出版)理所當然地邀他寫推介文字,結果就因為這個原因而無法使用。志清先生囑我當面代為解釋,希望他能見諒。在一次閒談中我若不經意地、試探性地提起。陳先生立即怒形於色;我囁嚅幾句適可而止。這篇文章他沒有給我看過。他為濟安師的追思會寫的Eulogy and Farewell(他自己譯為〈夏濟安先生哀誄〉)第二段說:‘His dear memory we forever deeply,vividly and earnestly cherish;and from the fine example of his personality as much as from his superb contributions to scholarship we continue to benefit’。這句話如果不用dear、deeply、vividly、earnestly、fine和superb等字眼已經可以達意,但他無疑力求情見乎詞。他為The Gate of Darkness這純學術性著作寫的Epilogue恐怕也有類似的渲染筆法。
從小學到研究所,最幸運的是遇到過幾個開我茅塞的師長。事業方面影響最大的除了恩師福爾斯特以外便是陳世驤先生。我始終銘記他的知遇之情,提掖之恩。加大本來就人才濟濟,聲譽卓越。(1960年代末期有一英國學者來美國實地調查各大學的優劣,最後認為整體而言以柏克萊為首選,超過哈佛。)又正碰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當口。在他身邊三年對我有深遠的裨益;至少開了眼界,長了見識。
陳先生中等個頭,但舉止凝重從容,看起來很有尊嚴,彷彿比實際身量高。而即之也溫,容易親近。做人處事他是很成功的。有時候回想起立委和院士等往事,聯想到他早期的鋒芒,不免為他感到委屈,惋惜;懷疑他那麼耗神費時,是否值得。以他深湛的學養,大可專心致志,精益求精,取得更豐碩的成就。
(下)
(此文脫稿後夏志清先生於去年12月29日辭世)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