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聲音》才 220元,很便宜。內容充實。推薦!

文學的聲音─三民叢刊238
- 叢書/系列名:三民叢刊/三民叢刊
- ISBN13:9789571435350
- 出版社:三民書局
- 作者:孫康宜
- 裝訂/頁數:平裝/356頁
- 規格:21cm*13cm (高/寬)
- 版次:初
- 出版日:2001/10/01
- 中國圖書分類:文學批評史
與劉先生談「文學的聲音」
輯一 性別的聲音
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
從文學批評裡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
末代才女的「亂離」詩
西方性別理論與漢學研究
輯二 經典的聲音
典範詩人王士禎
揭開陶潛的面具──經典化與讀者反應
劉勰的文學經典論
從「文類」理論看明傳奇的結構
「古典」與「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
輯三 抒情的聲音
擺脫與沉溺──龔自珍的情詩細讀
吳偉業的「面具」觀
《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
八大山人詩中的文學性與視覺性
輯一 性別的聲音
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
從文學批評裡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
末代才女的「亂離」詩
西方性別理論與漢學研究
輯二 經典的聲音
典範詩人王士禎
揭開陶潛的面具──經典化與讀者反應
劉勰的文學經典論
從「文類」理論看明傳奇的結構
「古典」與「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
輯三 抒情的聲音
擺脫與沉溺──龔自珍的情詩細讀
吳偉業的「面具」觀
《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
八大山人詩中的文學性與視覺性
與劉先生談「文學的聲音」
許多年以前,我早就希望能認識三民書局的老闆劉振強先生了。因為他所主編的那套「古籍今注新譯」一直是我的美國研究生們的必讀物。我的學生告訴我,他們很感激劉先生,如果不是他主編的那套以闡釋古籍為目的、以「兼取諸家,直注明解」為原則的「藍皮書」的幫助,他們肯定不會那麼快就熟悉中國古代的經典之作。作為讀者,他們特別佩服劉先生那種充滿信心的廣大視野(vision)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執著──這種執著的精神十分難得,尤其在今天出版社大多以賺錢和媚俗為目的的後現代世界裡。我認為學生們的觀點很對,我想劉先生當初一定是懷著發揚傳統典籍的理想才開始走向出版業這條路的。因此,這些年來,雖然我一直還不認識劉先生,但我們在課上時常提到他。「劉先生」早已成了三民書局的代名詞了。
去年六月,我終於有幸與劉先生面識,我們一見面就談得很投合。我發現我們有很相同的文學觀;我們都相信古典文學的不朽之魔力,都相信現代讀者有無比的詮釋之潛力。劉先生還告訴我,他最喜歡「做夢」,他的每項出版計劃都開始於一個夢──他主持有關「中國字」的龐大電腦工程即為一例。我還發現,劉先生的成功秘訣就是:一旦決定要做一件事,必定全力以赴,凡事不惜代價。他說,他的家人常問他:「你何時夢醒?」但他說:「如果沒夢,怎麼會有新的出版計劃?」
我告訴劉先生,我也是一個喜歡做夢的人。我的每個文學研究計劃也是始於一個夢。我喜歡堅持自己做夢的自由,哪怕我的想法有些不實際。詩人非默曾在〈堅持〉一詩中說過:「放棄幾乎是不可能的,/堅持的人不在乎這世界是否只剩下他一個。」在文學研究的道路上,我鼓勵我自己一直朝著理想堅持下去。
這些年來,我的夢想就是:努力捕捉古代文人才女的各種不同的「聲音」(voices)。我知道文學裡的「聲音」是非常難以捕捉的──有時近在眼前,有時遠在天邊;有時是作者本人的真實的聲音,有時是寄託的聲音。解構主義告訴我們,作者本人想要發出的聲音很難具體化,而且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十分錯綜複雜,不能一一解讀,因而其意義是永遠無法固定的。此外,解構批評家認為,語言本身是不確定的,所以一切閱讀都是「誤讀」(mis-reading)。另外,巴特的符號學則宣稱,作者已經「死亡」,讀者的解讀才能算數,在知識網絡逐漸多元的世界裡,讀者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文化主體,因此作者的真實聲音已經很難找到了。但近年以來,Stanley Fish所主導的「文學接受理論」雖然繼續在提高讀者的地位,卻不斷向經典大家招魂,使得作者又以較複雜的方式和讀者重新見面。在這同時,新歷史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都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努力尋找文學以外的「聲音」,企圖把邊緣文化引入主流文化。而目前流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其實就是這種企圖把邊緣和主流、把「不同」和「相同」逐漸會合一處的進一步努力。
自從一九八二年我到耶魯大學任教以來,由於面臨現代文學批評的前沿陣地(耶魯大學一直是現代各種文學批評的發源地),我一方面感到十分幸運,另一方面也給自己提出了警惕──千萬不要被新理論、新術語轟炸得昏頭昏腦,乃至於失去了自己的走向。我喜歡文學,喜歡聽作者的聲音,就讓我繼續尋找那個震撼心靈的聲音吧。回憶這二十年來,我基本上是跟著文學批評界的潮流走過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符號學理論、文學接受理論、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批評、闡釋學等諸階段。但不管自己對這些批評風尚多麼投入,我都一直抱著「游」的心情來嘗試它們的。因為文學和文化理論的風潮也像服裝的流行一樣;一旦人們厭倦了一種形式,就自然會有更新的欲望和要求。然而,我並不輕視這些事過境遷的潮流,因為它們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靈文化。對於不斷變化著的文學理論潮流,我只希望永遠抱著能「入」也能「出」的態度──換言之,那就是一種自由的學習心態。
於是,這些年來,我就持這種自由自在的態度陸續編寫了不少學術專著,希望能捕捉文學裡各種各樣的聲音。在《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一書中,我討論情愛與忠國的隱喻和實際關係,我曾借用Erich Auerbach的「譬喻」(figura)的概念來闡釋明末詩人陳子龍的特殊美學。後來,與Ellen Widmer(魏愛蓮)合編的Writing Women of Late Imperial China(《明清女作家》)──共收了美國十三位學者的作品──則側重於婦女寫作的諸種問題。不久前與Haun Saussy蘇源熙合編的一部龐大的選集《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共收了六十三位美國漢學家的翻譯──則又注重中國古代婦女的各種角色與聲音。那本選集中的材料多半是我八○年代以來花了不少精力時間和財力才終於收集起來的。(上海的施蟄存先生在我收集材料及構思的過程中,曾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特此感謝。)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那會是一個極其浩大繁重的編輯過程,但我很高興我終於堅持了自己的夢想。我總是希望能通過大家共同的翻譯與不斷闡釋文本的過程,讓讀者們重新找到中國古代婦女的聲音──書中共收了一百三十位左右的古典女作家作品,加上五十位男女評論家的文字。總之,我一直盼望能藉此翻譯編撰的過程,讓美國的漢學家們開始走進世界性的女性作品「經典化」(canonization)行列,從而把中國女性文學從邊緣的位置提升到主流的地位。
此外,我告訴劉先生,我在研究各種文學聲音的過程中,也逐漸發現了中國古典作家的許多意味深長的「面具」(mask)美學。這種面具觀不僅反映了中國古代作者(由於政治或其他原因)所扮演的複雜角色,也同時促使讀者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闡釋作者那隱藏在面具背後的聲音。所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解讀一個經典詩人總是意味著十分複雜的閱讀過程──那就是,讀者們不斷為作者戴上面具、揭開面具、甚至再蒙上面具的過程。在有關陶淵明、《樂府補題》、吳偉業、八大山人、王士禎和「閱讀情詩」等幾篇論文裡,我曾先後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
劉先生說,三民書局希望能出版我的論文集。我說,那麼,就把這個論文集取名為《文學的聲音》吧。收在這裡的幾篇學術文章也正代表了我近年來叩問古典文人的心聲的旅程。羅蘭‧巴特曾說過:「閱讀是一種樂趣,這主要是因為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探險。」但對於我,閱讀不但是一種探險的經驗,也是與其他讀者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報告的好機會。
在此,我要感謝陳磊、皮述平、錢南秀、王璦玲等人,他們把我的幾篇英文學術論文譯成中文。但這個論文集之所以能及時出版,主要還是由於三民書局編輯部諸位同仁們的努力幫助,他們嚴謹的工作態度,都是一流的。
二○○一年七月四日寫於耶魯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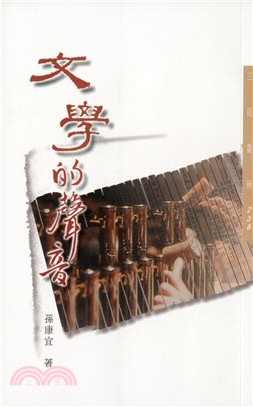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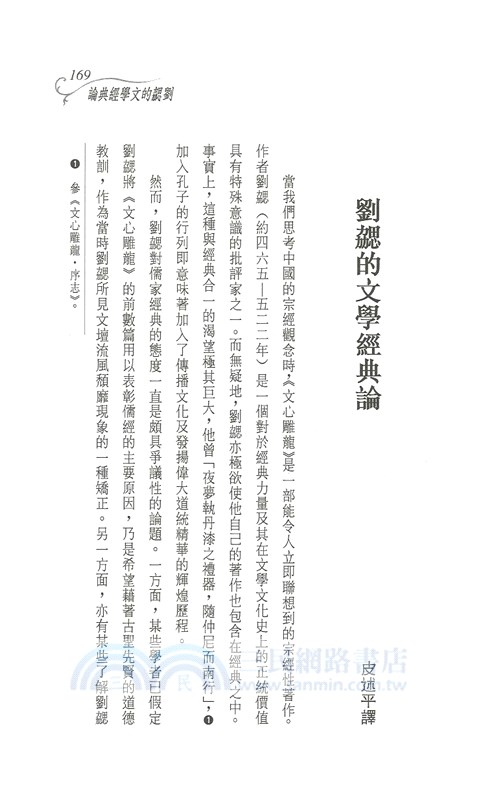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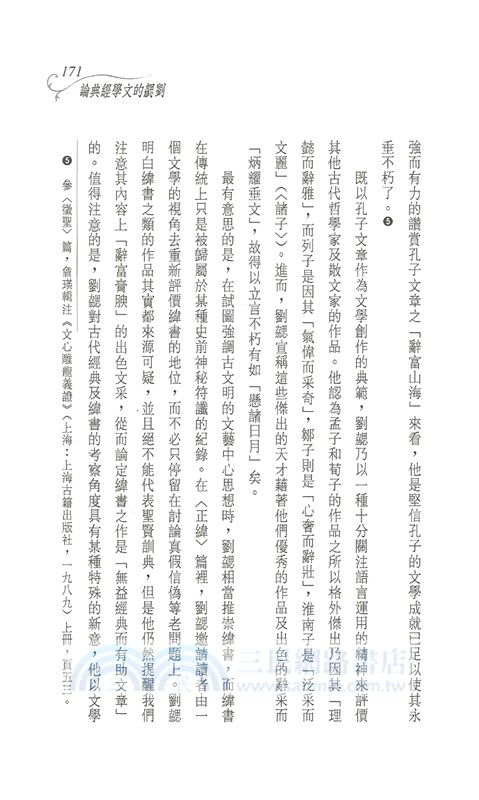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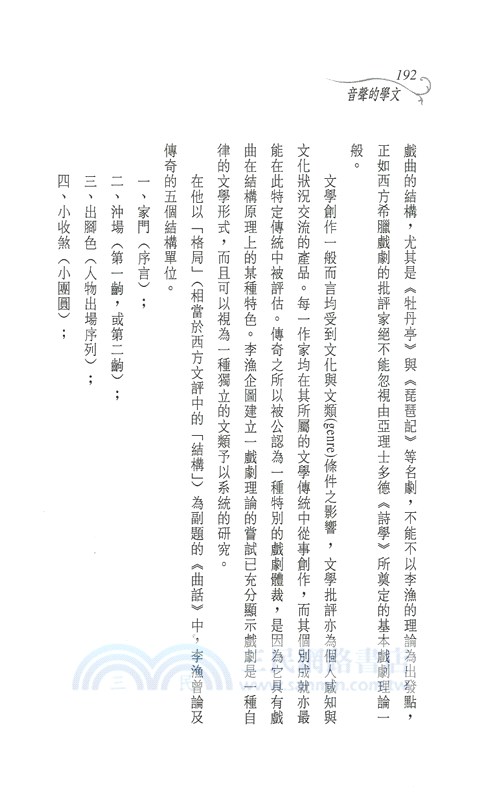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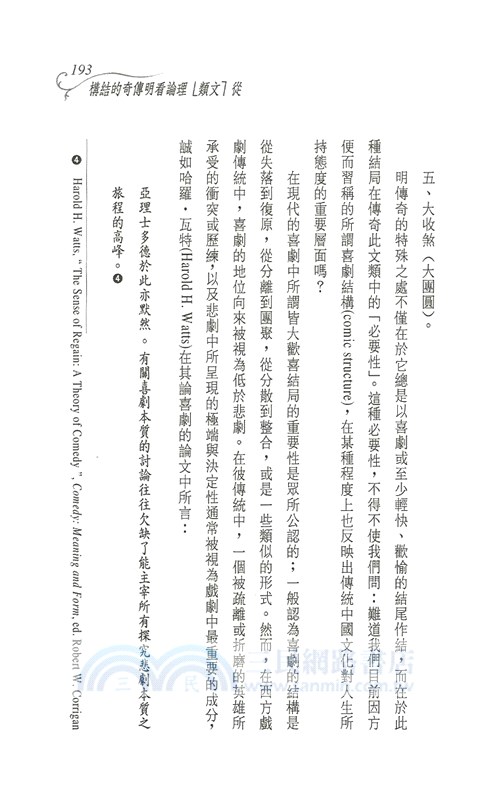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