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ISSN 0257-0270;CN 11 1073/G2)是一份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人文學術月刊,創刊於1979年。內容以書評為主,多為學術性探討。
《<讀書>創刊三十周年告讀者》一文稱,該雜誌自創刊即定位為「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既有別於專業學術研究刊物,也有別於一般大眾通俗刊物,讀者對象為關注思想文化領域及相應書籍出版的中級以上知識分子(《讀書》2009年第4期第167頁)。
主要欄目:書評、著譯者言、短長書、讀書平台、讀書短札等。
漫畫家丁聰從創刊起曾長期為該雜誌繪製漫畫,每期兩幅,內容一般為針砭時弊,並曾設計版式。目前,每一期的封二為「畫說」欄目:黃永厚作畫,陳四益撰文。書內另有趙汀陽漫畫一幅。
值得思考的是,約1990年代末,《讀書》在台灣、香港等發行繁體字版,可能一兩年就陣亡了。
***
舊書店買到揚之水 3冊之一的《讀書》十年(一)
《讀書》創刊於1979,是本給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娛樂/知識"月刊。
揚之水現在已著作等身。她當年當"編輯/跑腿"時的記事本之剪裁後"日記"。每一年卷前有名人 ( 揚之水甚得一些老作家的喜愛,常供稿不斷)的賀年卡或簡涵。
我之後會補上兩張掃描。《讀書》的人物由丁聰根據複印照片重畫,有張Walter Benjamin的,沒刊過。
另外是讀書筆記,比較《神曲》《約翰克利斯朵夫》兩譯本的句子。
這本書紀許多買書,書名至少上千本,譬如《台灣的中國文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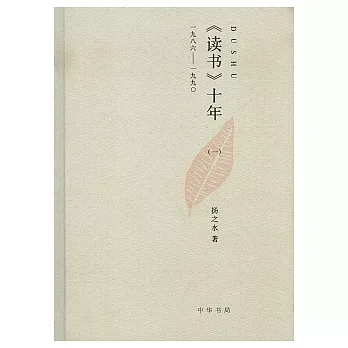
《讀書》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
- 作者: 揚之水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日期:2011/11/01
- 語言: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1986年到1996年是當代中國社會不同尋常的十年,也是中國思想學術界經歷了興奮、挫折與彷徨的十年。《讀書》這份三十年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人文思想雜志,見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歷程,與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深刻變化。本書以《讀書》編輯部的日常事務、編著往來為中心,記錄了當時與《讀書》發生往來的知識界的種種情況,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化。《〈讀書〉十年》系列的第二集(1991—1993)、第三集(1994—1996)將陸續出版。
揚之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諸暨人,長在北京。初中畢業後插隊,回城後為果品店司機。一九七九年調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資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調入《讀書》編輯部。一九九六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意從事名物研究。著有《詩經名物新證》、《詩經別裁》、《先秦詩文史》、《古詩文名物新證》(兩卷);《終朝采藍——古名物尋微》、《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三卷)。其中《奢華之色——宋元明金銀器研究》(三卷)、《詩經別裁》等由中華書局出版。
目錄
序一(沈昌文)
序二(吳彬)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年
後記一
後記二
序
上天安排,讓我在二三十年前認識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實的小女子︰揚之水。
我那時在三聯書店工作,具體負責《讀書》雜志的編務。《讀書》是出版界名流陳翰伯、陳原和範用創辦的。我進去後發現,編這雜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剛挨過大整恢復名譽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陳翰伯找來的馮亦代。馮先生那時已年過六十,過去是外文出版局的專家,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專長是美國文學,是黨外的著名外國文學專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會活動。他在文化界號稱“馮二哥”,以善于排難解紛著稱。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禍從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c,又被打成“美蔣特務”、“二流堂黑干將”、“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後多年勞役摧殘。現在他剛恢復名譽,復出任職,自然干勁十足。陳翰伯可謂識人。
另一個副主編倪子明,是範用多年的老戰友,出版總署的一位老處長。他是老黨員,在黨內挨過整,說他是“胡風分子”,因為他認識胡風。這位老黨員是位少說話多于事的老實人。連他這樣的人,過去也要挨整,現在想來,依然覺得奇怪。他黨齡很長,因此在編輯部地位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編齡”說,他最長。他曾是老共產黨員,據說胡繩當年都還是他介紹入黨的。範用聘他擔任執行主編,讓我十分驚訝。因為範用當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辦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劃上“右派”的。現在作此安排,可見改革開放那些年頭思想解放的深度和範用他們的膽略。
因馮亦代的關系,又引進了著名的畫家丁聰來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馮亦代一樣,為人“四海”,廣交朋友。馮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別談得來。
三聯書店名義上是家有幾十年悠久進步歷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時卻落得個“房沒一間、地沒一壟”的悲慘境地。我們在北京好幾個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辦公。編《讀書》的都是經過浩劫復出工作的大牌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其忙無比。因此,編輯部內十分需要操作具體編務的助手。那時能找到的都是剛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們中間找對書本和知識感興趣的年輕人。好在我們這些行政上的所謂“領導”,普遍學歷都是初中。當時的實際負責人董秀玉女士,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畢業生。我本人更加特別一點︰正式學歷是初中一年級。而最早我們聘用的一位同事,是從雲南建設兵團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級學生吳彬。還有一位當今的大學者,王焱,當年進《讀書》工作以前是公交車上的售票員,也是初中一年級學生。那些老前輩覺得這麼一些中學生當他們的助手,也還得心應手。因此,我們對這些知青,一點不歧視。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紹一位女士加入編輯部。她過去為《讀書》投過稿,不算陌生。一看簡歷,頗不簡單。這“不簡單”,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過學,等等。幾十年前,這位揚之水小姐的“不簡單”卻是︰讀過初中,插過隊,做過售貨員,開過卡車,等等。卡車司機居然對文字工作感興趣,而且確實在《讀書》發表過文章,令人驚訝。大家覺得合適,于是錄用。
這樣就同這位女士成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卻往往“訥于言”,讓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細。只記得,某日,我忽然請她背誦黨綱,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覺得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過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編政治讀物,所以我只會這樣考核部下。
她年輕,肯走路,于是經常派她出去取稿,實際上是做“交通”。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學者,對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學,所以訪行以前必作充分準備。可是金老同揚之水更談得來。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來五篇,都請她代為處理,他對揚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張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對她極有好評。張中行先生對揚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寫了一篇談揚女士的專文,居然說︰“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沒有離開書,可是談到勤和快,與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風。”作者和編輯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實為我畢生所僅見。
我到了多年以後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聯絡當作一種“師從眾師”,所以十分得益。她說過︰“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讀書》,一直到一九九六年。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在《讀書》認識的作者都是頂尖人物。這對于我來說是‘師從眾師’了。不限于某一老師,這樣就不會有一種思維定式,視野就更開闊了。那種幫助是一種影響,等于是在他們中間燻陶出來。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這方面受益就特別多。他特喜歡陳散原的詩,我幫他借,借完以後我自個兒又抄了好多,全都是營養。”
一九九六年,揚之水與我同時離開三聯書店。我是退休,她是轉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以後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舉。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論著,于是人們問起她,我往往回答說︰她現在在開文化卡車。她在文化大道上駛行不休,暢通無己,委實高興。
《讀書》雜志在前輩的帶領下,在吳彬、王焱、揚之水這麼一些中學生的實際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輩的帶領下,一大批初中生們的促進幫助下,慢慢地、不得己地蹣跚前進;而揚之水這位卡車司機,怎麼能在《讀書》雜志打工若干年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如此熟練地馳騁在文化學術的大道上,這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謎。要知道謎底,請一讀揚之水女士的這本日記。
沈昌文 二○—○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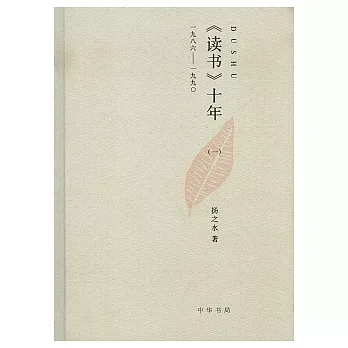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